9月26日下午,beat365“英美文學經典的人文理解”系列講座第四講在文南樓204會議室順利舉辦。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于雷教授以“《被盜的信》:秘密寫作、邊緣視野與表層閱讀”(“The Purloined Letter”: “secret writing,” “peripheral vision,” and “surface reading”)為題進行演講。本次講座采取線上線下結合模式,來自校内外約300名師生聆聽了講座并參與讨論。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陳雷教授擔任與談人。講座由beat365歐美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曹莉教授主持,華東師範大學金雯教授、beat365王敬慧、陳湘靜、趙元、沈安妮等師生線下參會。
講座以《被盜的信》為中心,在認識論層面上探讨了“秘密寫作”“邊緣視野”及“表層閱讀”等文學議題,通過闡釋學、密碼學、圖像學、眼科學等跨學科研究視野分析了小說的加密書寫與解碼機制,同時也為讀者如何閱讀文本提供了生動的實踐範例。

于雷教授講座
于雷教授分别梳理了“秘密寫作”“邊緣視野”及“表層閱讀”等三個關鍵概念的定義及其理論來源,并詳細分析了三者與文本的結合點與生發點。坡認為秘密寫作這一文化意象由來已久,他關注到古代斯巴達人曾運用“圓筒配對法”( scytale)進行信息加密。
坡甚至在其短篇小說《金甲蟲》(“The Gold Bug”)中通過海盜的藏寶圖對秘密寫作進行了寓言化的呈現。“邊緣視野”指的是“用眼角餘光或視網膜外圍去審視”,美國華裔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 Tuan)在《戀地情結》(Topophilia)中提到的“邊緣視野”與坡主張的“側目而視”(sidelong glance)不謀而合。“表層閱讀”這一概念來自于美國學者貝斯特(Stephen Best),他曾撰文強調,文本隻有二維幾何學意義上的長度與寬度,并無“厚度”,文學闡釋的核心在于“看到”(look at)而非“看穿”(see through)。值得注意的是,貝斯特在文中還特别提及《被盜的信》對于表層閱讀的原型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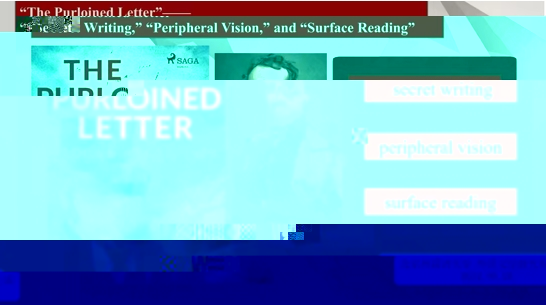
于雷通過梳理小說的主要情節指出,小說的兩條關鍵邏輯分别為“盜信者知道失信者知道盜信者”以及“簡單是通往複雜/深度的路徑”;兩者既是故事叙事結構的内在邏輯,又是元語言意義上的閱讀認識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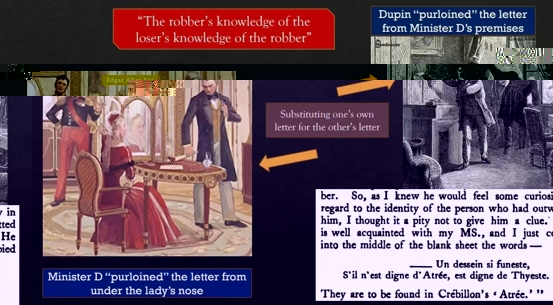
講座聚焦于拉康曾關注過的來自荷爾拜因(Hans Holbein Jr.)的《大使》(“The Ambassadors”)那一畫作,分析其中的視覺失真機制,進一步說明“邊緣視野”和“表層閱讀”如何将深層闡釋傳統還原為其事實上的表層邏輯。“邊緣視野”具有認識論意義上的普适價值,它要求闡釋者充當一名合格的文學偵探,不能簡單依賴于《被盜的信》中的警長G先生所采取那種基于純粹數學理性的線性思維,而是要扮演詩人與數學家之雙重角色,将杜賓所熱衷的非線性思維植入到傳統的深層闡釋當中。在這方面,十九世紀意大利藝術鑒賞家喬萬尼·莫雷利(Giovanni Morelli)以及當代哲學家齊澤克的“斜視”(looking awry)均為我們提供了範例。其重點在于,關注文本邊緣信息對總體結構的功能性影響,讓看似無關緊要的瑣碎信息發聲,由此更為系統地捕捉文本結構的層次,使得中心與邊緣之間的辯證關聯得以顯身。為了更加清晰地說明《被盜的信》何以成為一種閱讀認知的寓言,于雷以《大使》的相關闡釋為例,指出數個世紀以來,人們大多被畫面正下方那一小片入侵的神秘色塊所吸引,卻忽略了畫面中原本最顯而易見的兩位大使;他們是誰?兩者站立的肖像畫與文藝複興時期的雙人肖像畫有着怎樣的區别?當我們借助“斜視”發現隐身其間的“骷髅頭”那一視覺失真的秘密之際,兩位大使存在的意義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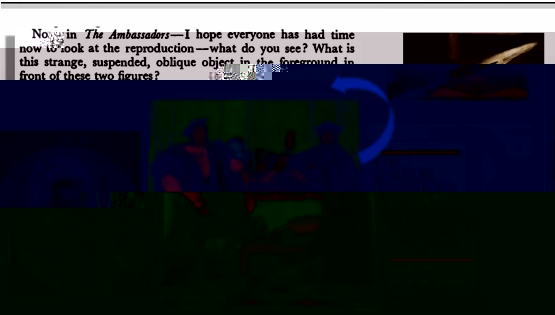
于雷在此引入以色列學者凱南(Hagi Kennan)的闡釋,再次強化了文本闡釋進程中訴諸邊緣視野的重要價值,但與此同時又提醒我們,關注邊緣本身并非目的,而是為了從系統論意義上厘清邊緣與中心的辯證互動:掌握了“骷髅頭”在文藝複興時期雙人婚典肖像畫中的隐喻内涵将從一個邊緣化的視角幫助我們重新審視中心地帶的兩位男性大使之間的那“無以命名的愛”。從邊緣反顧中心往往更容易窺見文本中的盲點,一如坡在《被盜的信》中所論及的“既是詩人又是數學家”,使價值理性成為工具理性的評價者與引導者。
講座進一步讨論了19世紀電磁電報時代與秘密寫作的文類關聯:坡所開創的象征主義詩歌與偵探小說在麥克盧漢看來正是對電磁電報這一19世紀新媒介作出的詩學回應。二者的共通點在于通過高度凝縮的具象化能指将意義藏匿于表象之後。為了更好地說明坡的秘密寫作背後的媒介技術話語,于雷為《被盜的信》找到了一個有趣的“腳注”——坡的另一則更趨元語言意義的短篇小說——《X出一個段落》(“X-ing a Paragrab”)。兩者看似毫無關聯,但于雷注意到“letter”這個字眼的雙關性(書信/字母)——“被盜的信”成了“被盜的字母”,小說中的排版工不得不以X 臨時替代被盜的字母 O,這種“缺席的在場”卻意外使文本獲得了語義增殖。作者決定了“怎麼寫”,同時也預設了“怎麼讀”,而邊緣視野則成了作者與讀者的認知博弈——讀者唯有通過“邊緣視野”對文本進行“表層閱讀”才能如杜賓偵探那般揭示作者的“秘密寫作”機制。
于雷最後提到,一切小說文本都是各具特色的有機生命體,擁有自身的内在邏輯,讀者應當尊重那種個性化的邏輯;與此同時,闡釋者應當以文學偵探的姿态留意文本表層現象世界中的瑣碎細節,不帶偏見地對其進行平等處理,真正建構中心與邊緣的辯證關系。于雷教授将《被盜的信》視為認識論棱鏡,重新審視莫雷蒂(Franco Moretti)提倡的“遠讀”批評實踐,指出遠讀與細讀并非二元對立,正相反,遠讀的核心基礎恰恰是基于邊緣視野和表層閱讀的細讀,就像納博科夫所說的“将閱讀文本變成觀看畫卷”,一方面抵抗線性閱讀進程所無法回避的遺忘機制,另一方面也抵禦深層闡釋傳統的誘惑,學會尊重閱讀進程中最真切的直覺體驗,從而使文學批評真正體現人性的本真與不乏趣味的人文情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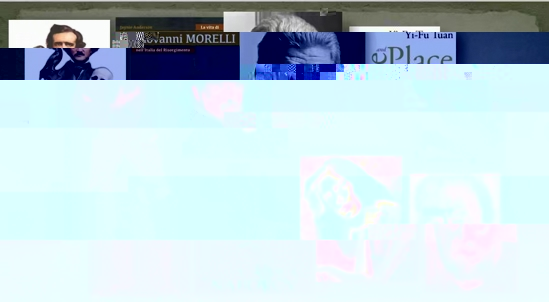
在與談環節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陳雷教授就“邊緣視野”因何而重要這一核心議題進行了點評。陳雷教授認為,觀者通過“邊緣視野”更易捕捉事物的主體輪廓,遠看和近看、遠讀和細讀并不矛盾,而應該有機結合在一起。同時,他提到“邊緣視野”與19世紀浪漫主義時期的想象觀(imagination)有所關聯,譬如柯勒律治(S. T. Coleridge)将想象力劃分為理性(reason)及智力 (intellect),理性本身就包含着詩性的想象。坡借由“邊緣視野”來捕捉事物的主體輪廓,是一種直覺地把握真相的能力,與科勒律治所謂的想象和理性意義接近。此外,他提到表層閱讀的重要性,并以法國點彩派畫作為例說明形象并非隐藏其中,而是展現于其表,自然奧秘即在眼前,一如《莫格街兇殺案》中所有的線索一開始就展現在衆人眼前一樣。最後,陳雷表示,秘密寫作實際上是設謎與解謎的過程,這一行為在遠讀及細讀的循環往複中得以不斷生成。

陳雷教授與談
華東師範大學金雯教授在發言中表示, “beat365英美文學經典的人文理解“系列講座回答了文學闡釋的本質和根本任務是什麼這一重要命題,她認為“表層閱讀”是對深層闡釋傳統的反向補充,文本無盡的表層經驗會導向讀者對文本的發散性的閱讀體驗,這給文學研究帶來了挑戰,但同時也是機遇。線上線下的同學也圍繞講座中三個關鍵議題之間的邏輯關聯、“缺席”與“在場”之間的張力關系、技術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辯證關系等問題展開熱烈讨論。

金雯教授發言

現場同學提問
文|侯楠
圖 | 道日娜
編輯|沙克爾江
審核|高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