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晚上,beat365“英美文學經典的人文理解”系列講座第二十二講在文南樓 216 會議室如期舉行。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毛亮以“愛默生的《論美國學者》:文本與事件” 為題進行演講。本次講座采取線上線下結合模式,來自校内外約200名師生聆聽了講座并參與讨論。講座由beat365beat365副教授陳湘靜主持,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于雷擔任與談人。
講座以《論美國學者》(“The American Scholar”)為中心,結合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教育經曆、寫作與哲學思想,以及當時美國社會的民主文化和道德價值觀,對經典文本進行了創新解讀和重新定位,點明愛默生在《論美國學者》中對智性自由、智性民主的推崇,同時也為讀者如何解讀文本、理解曆史事件提供了生動的實踐範例。

1837年發表的《論美國學者》是愛默生成熟期之前的作品,也是他接受了浪漫主義唯心論之後初步完成的三部作品之一。另外兩部分别是1836年出版的《論自然》(Nature)和1838年發表的《神學院講演》(“Divinity School Address”)。三篇分别從哲學、文化、宗教三個方面對美國文明中的核心問題做出思考和反思。
《論美國學者》可以被視為愛默生初步運用浪漫主義唯心論邏輯的寫作,1840年之後幾年中分别出版的《散文一集》和《散文二集》(Essays, First and Second Series)則标志着愛默生文學和思想成熟期的開始。《論美國學者》被許多學者解讀為論證美國文化獨立性和美國文學特殊性的文本,甚至被認為是“美國文化的獨立宣言”。毛亮教授對這種論斷提出質疑,并将《論美國學者》重新定位為對新英格蘭哲學、宗教、文化的現狀及未來方向的檢讨和思考,乃至對當時美國民主文化和價值體系的反思與颠覆。

從教育經曆看,愛默生在哈佛大學接受的是傳統、保守的新英格蘭紳士階層教育。這種教育在哲學上表現為英國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和蘇格蘭常識哲學(philosophy of common sense);文學上呈現典型18世紀英國散文風格,講求理性邏輯和文字文雅(propriety);宗教上以一元論(unitarianlism)為主,注重理性,強調正統的基督教義。愛默生的思想卻與這種教育主張相背離,轉向了浪漫主義和唯心論。毛亮教授特别提到聖經批評(higher criticism)對愛默生宗教觀點的影響,促使他成為一個世俗化(secular)的學者。
講座進一步指出,《論美國學者》的發表是美國文明演進過程中的一次重要轉變,同時具有文本和事件兩個層面的意義。毛亮教授引用了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論文《尼采·譜系學·曆史》(“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中對“事件”(event)的論述,指出《論美國學者》的發表是一曆史事件,它帶來了新的文化思想,标志着新的人性觀、價值觀進入美國文化。
當時美國社會流行的道德價值觀是基于官能心理學(faculty psychology)對人性的理解(即“the mechanical scheme of empowerment and constraints”),認為人性是由三種力量組成的,分别是經驗主義的理性(reason),強烈的心理驅動力(passions)和審慎(prudence)。這種道德哲學強調對欲望的克制和引導,培養審慎的理性選擇,達到内心力量的平衡與制衡(equilibrium and balance)。相應地,由紳士階層領導的精英主義民主也強調秩序、約束、标準,反對平等的政治參與;文學上也相當保守,主張克制人性,教化、引導和約束一般民衆。
《論美國學者》發表于1837年,此時的美國正經曆經濟危機和憲政危機,民主的基本原則和價值觀受到沖擊破産,各方矛盾無法調和,自由競争理念和制衡機制失效。這也成為了《論美國學者》的寫作背景,正如愛默生在文中寫道,“Let me begin anew”,重新建立社會道德的底層原則。
愛默生使用了“整全人格”(whole-man)這一浪漫主義哲學概念,強調人性内在的統一(unity)和人性自身演變、成長的特性(progressiveness),與18世紀人性觀(mechanical view)形成對立。《論美國學者》中提出的“Man Thinking”強調智性活動的過程,将其置于人性的核心位置,而非18世紀人性觀強調的“審慎”(prudence)。至于如何培養完整的人性、實現智性自我的成長,愛默生提出了三個方面(nature,books,action),可分别解讀為客體,傳統,以及社會行動。客體的作用在于實現人的智性自覺,通過自然和其他客體,達成自我意識的發現(“know thyself”)。這種觀點體現了浪漫主義和唯心主義色彩。愛默生強調在智性的基礎上,對待傳統應該采取對抗的态度,而非一味地崇拜和尊重。愛默生還指出經驗能夠為自我意識、智性的成長提供資源,并通過社會行動成為思考的對象。這三者,即自我意識、文化傳統和社會行動構成了新的有機體,颠覆了原本的政治道德基礎(moral-political infrastructure)。這種對智性活動本身的依賴也體現在愛默生1841年發表的《論自助》(Self-Reliance)中,影響了愛默生對所處時代的樂觀評價以及他的作品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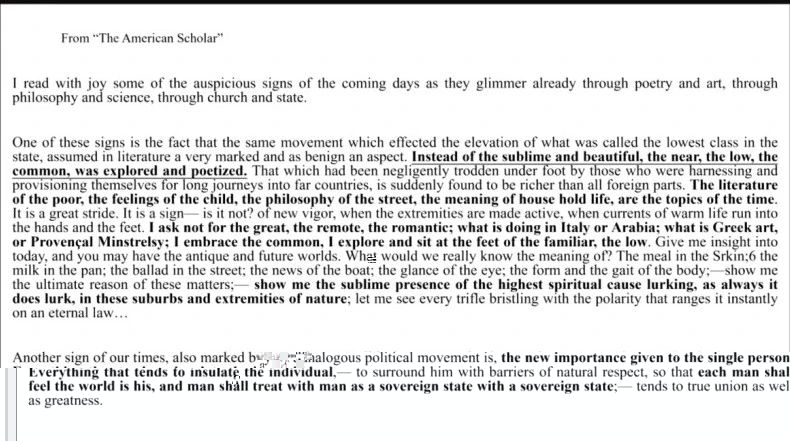
愛默生在《論美國學者》中展現出在智性自我的前提下,美國文化有可能形成的新觀念和寫作風格,一種新的修辭的可能。“Instead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the near, the low, the common, was explored and poetized...”當人有了智性自覺的能力,就能夠把經驗中的細節變成思考的對象;由此一來,任何事物都可以成為象征,正如文本中的“the milk in the pan”“the ballad in the street”。愛默生喜歡使用的“高低搭配”,例如“literature of the poor”“philosophy of the street”也體現了這一觀點。這種思想也對文學創作的風格産生了影響,如惠特曼(Walt Whitman)和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詩歌創作。

講座最後,毛亮教授對如何理解《論美國學者》進行了總結,指出不應從美國文化獨立性或是美國文學特殊性的角度去閱讀這篇文章,而應該考慮其對于價值論、人性論的颠覆性讨論。愛默生試圖通過《論美國學者》在民主理念中建立一種新的、智性自由的維度,探讨将其作為民主基礎的可能性。智性自由強調一種非功利的思維方式,尊重個體,認可智性活動的力量和人的内在不斷成長的可能。這種理念連接了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創造性地指出了制度本身蘊含的一種可能性,即用智性民主來解決美國社會的各類問題。

在與談環節中,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于雷教授就講座的思辨性和深刻性進行了點評,并為《論美國學者》的文本解讀提供了補充性的維度。于雷教授認為,毛亮教授不乏有趣地提及愛默生與愛倫·坡(盡管二人之間的私人關系較為緊張)在質疑民族文學這個議題上所表現出的難得的默契。正如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布爾(Lawrence Buell)在論述“愛默生美學”之際從愛默生的警句文體風格中所揭示的那種超民族性。于雷教授認為,這确實與愛倫·坡對民族文學的質疑存在相似之處。于雷教授還注意到文本中所流露出的“珍愛命運”(amor fati)之主題——這也正是尼采哲學中的要素:生命中的一切事物無論好壞都有其價值,并且可以成為智性成長的曆程。此外,于雷教授還特别強調《論美國學者》中所主張的“創造性閱讀”(creative reading);創造在愛默生那裡不止于物的創造,更意味着思想的創造。這種對創造性的關注讓我們想到了意大利哲學家維柯(Giambattista Vico)所提出的“真理即創造物”(verum factum)理念,也即真理與創造物可以互相轉換。這對于理解愛默生哲學思想中的宗教世俗化取向有一定的價值。最後,于雷教授引用了尼采對愛默生的評價作為結語:“愛默生有一種寬厚聰慧的快活性情,足以消解一切認真态度;他全然不知道自己已多麼年老以及将多麼年輕。”

文|杜宣熠
圖 |毛亮 李佳靜 杜宣熠 張曉婵
編輯|沙克爾江
審核|高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