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蘭·羅素,1872年出生于英國威爾士曼摩斯郡一個顯赫的貴族家庭。1890年,他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1908年成為學院的研究員并獲選為英國皇家學會院士。距今一百年前的1920年秋天,在張崧年和梁啟超的促成之下,羅素受講學社之邀前往北京大學講學。
羅素首先是作為一個哲學家被邀請,但在當時為中國謀求新的出路的各派知識分子眼中,他的政治和社會觀點更被期待和重視。在歡迎羅素的緻辭中,梁啟超代表講學社對羅素來華講學提出了期許。梁啟超說,講學社渴望聽取任何在促進中國文化進步方面有價值的理論,中國願意聽取甚至引進西方的思想和理論系統,包括還沒有在西方實踐成功的,提出希望羅素不僅講哲學問題,更要就社會和政治問題發表意見。
彼時,48歲的羅素正值盛年,不僅在邏輯學和哲學方面成就斐然,他作為政治和社會思想家也已享譽世界,在中國更是被冠以“世界最著名哲學家”的稱号,受到諸多知識分子的崇拜。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貧弱的中國面臨内憂外患,有着強烈的救亡圖存的危機感,五四新文化運動剛剛開始,全盤西化的激進呼聲也日益高漲。羅素對西方在中國的影響深感憂慮,他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對于自己所造成的他人的苦難熟視無睹,希望在中國可以找到治愈西方各種頑疾的良藥。在中國近一年的時間裡(1920年10月-1921年7月),羅素不僅在北京大學開展多個系列講學,更受邀前往上海、杭州、南京、長沙、保定等多地演講,反響很大(負責為其翻譯的正是趙元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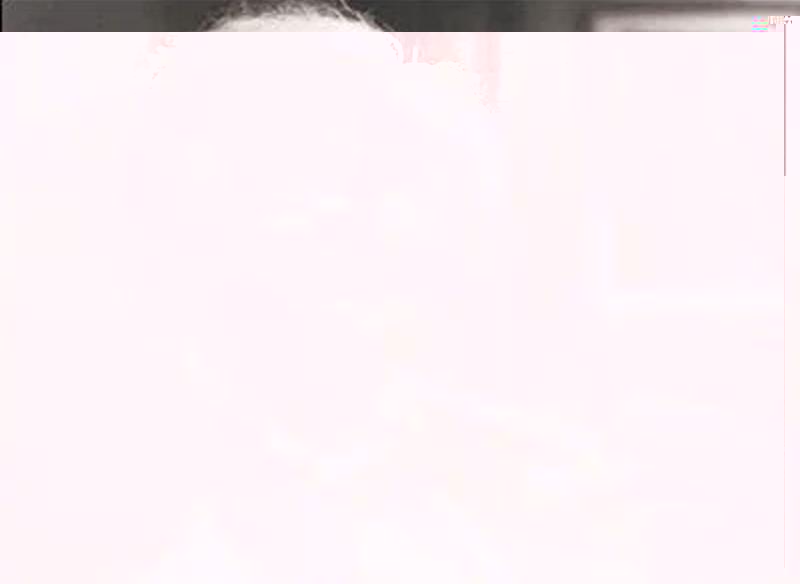
伯特蘭·羅素
羅素對當時西方人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深惡痛絕,認為他們正以辦工廠、銀行、建醫院和教堂的流水線方式,一邊破壞又一邊試圖修補中國人的肉體及靈魂。羅素極為欣賞中國的文化和生活哲學,雖然在中國期間曾身染重疾,卻依然對在中國的時日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在1921年初寫給一個朋友的信中,羅素寫道:“我在這個地球上沒有家——于我而言,中國比任何地方都更有家的感覺,因為這裡的人毫無暴戾之氣。”
一個世紀前的中國,正處于思想和政治變革的關鍵時刻。各派知識分子都認為中國的主要問題集中在三方面:經濟落後、政治分裂、政府無能。他們希望羅素的見解可以幫助提供一些應對中國問題的方法。羅素在北大和中國其他地方進行了一系列的講座,聽衆最感興趣的就是他有關社會構造和政治革新的内容(他講的更專業的邏輯學和分析哲學一般人也聽不懂)。但羅素的幾個系列講座并沒有對彼時的中國社會産生實質性的影響。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哲學家羅素在分析社會及政治問題時,喪失了其對待哲學問題時所持有的客觀性、分析能力以及科學方法,他個人的偏見阻撓了他對社會形式的科學分析。他在講座中對重建中國所提出的方案和辦法并沒有受到重視。但羅素回國後所寫成的《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一書,尤其書中對于中西文明之對比、對中國人的特點和中國傳統之特質的分析卻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持久的讨論。
《中國問題》是羅素1921年夏回國之後所寫,1922年在英國和美國同時出版。書中雖有對中國社會種種弊端的直言不諱,但更多的是對中國的曆史文化及中國人的贊賞。孫中山先生因此書而稱羅素為“唯一理解中國的西方人”,羅素也因此書而成為當時西方讨論中國時必然提及的人物。那麼,這本書說了什麼呢?筆者将簡單介紹一下羅素在書中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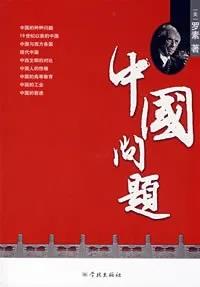
中國問題
羅素開篇即指出,即便是與其他任何國家毫不相幹的“中國問題”,也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原因就是中國人口占據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羅素斷言,“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中國的發展将對全世界産生極為重大的影響”。他指出,在對一個社會作出判斷時,不僅要看這個社會内部有多少的善與惡,還要看它是否造就了其他社會的善與惡,以及它所享受的善多大程度依賴于它在别處所犯下的惡。羅素認為,西方的繁榮是依靠恃強淩弱所得,而中國則是依靠自己的美德和勤勞。
羅素對中國人自身的各種品質大為贊賞。他認為中國人性情溫和,能苦中作樂。“無論哪個階層的中國人”,羅素贊歎,“都比其他任何國家的人更愛笑。他們似乎在任何事情中都能發現可樂之處,任何争執也都能被一個玩笑化解。”“中國人由上至下,都有着無法侵犯的平靜的尊嚴,包括苦力在内”。羅素最為佩服中國人自得其樂的能力。他發現即便是最貧窮的中國人也比一般的英國人快樂的多,他認為這是因為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思想根基就比西方更加人文也更加文明,而西方的躁動與好戰使得人們幾乎喪失了思考的美德和欣賞美的能力。羅素認為這也是中西方交流很可能是互益互利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可以學習不可或缺的西方科學和技術,而西方可以學習中國精神和文明方面的智慧,因為正是這種智慧才使得中華民族成為世界上屹立不倒的古老文明。中國物産豐富,人口衆多,完全能一躍而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強國”。羅素認為,為追求獨立自主、自立自強,中國必然要向欺辱她的西方列強學習科技、工業和軍事,但如果中國在如此強大自身的過程中,也變得像西方列強那樣恃強淩弱,抛棄自己文化中寶貴的公正和價值,那麼中國即便強大起來也是一種失敗。
在對中西文明進行對比時,羅素首先指出,曆史上不同文明的接觸和交流都促進了人類進步:古希臘學習古埃及,古羅馬學習古希臘,阿拉伯國家學習羅馬帝國,中世紀歐洲學習阿拉伯國家,文藝複興時期歐洲學習拜占庭王國等。不同文明互相交流學習的過程中,很多虛心學習的學生最終取得了比自己的老師更輝煌的成就。如果把當時的中國視為向西方學習的學生,那麼這個學生很可能再度超越老師。羅素認為,西方同樣需要向中國學習,但由于西方自視太高不可教,所以不會去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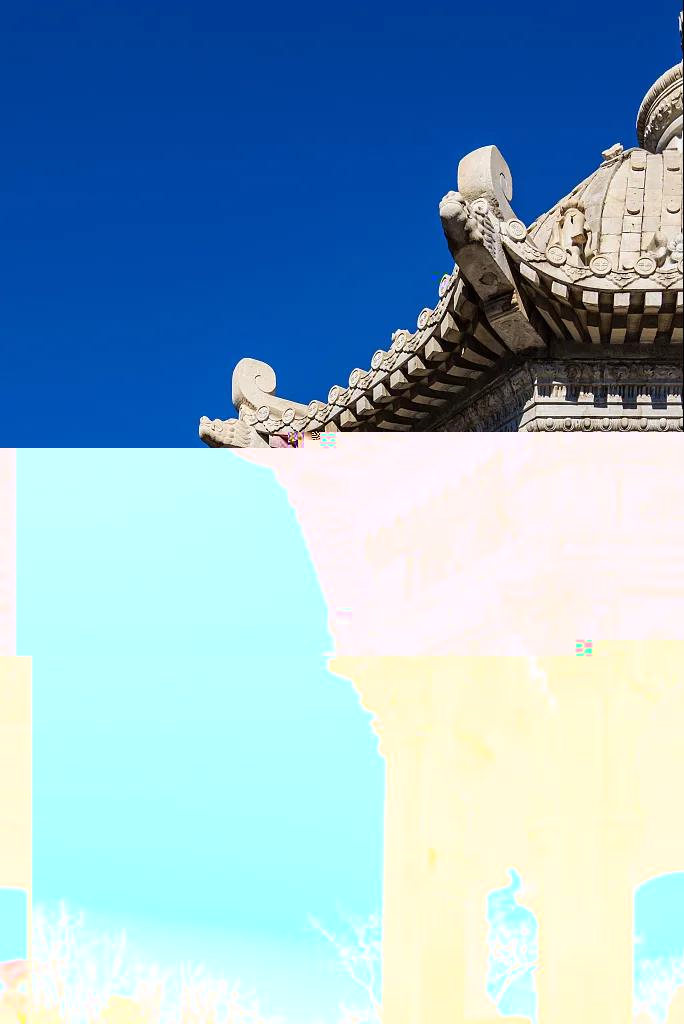
中國這個古老的文明和西方相遇的結果會是什麼呢?羅素決定抛開政治經濟層面,僅從思想和文化的角度來讨論。當時的中國迫切想要向西方學習,不全是為了增強國力抵制列強的侵略,而是因為許多中國人認為學習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中國人自古重視知識的學習,以前認為古典經文才是知識,而現在普遍意識到西學更加有用,也希望快速革新國人的舊思想。羅素說,當時中國人一心向學的熱情,讓他想起15世紀意大利的文藝複興精神。而且,中國人學習西方是有所取舍的,尤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暴露西方各種危機之後。羅素指出,中國人必須運用自己的智慧,有機結合中西文明之精華,才能達成自我救贖。羅素用老子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持,長而不宰”來說明中國人在思想上優于西方。和西方相比,中國征服統治其他族類的欲望要小得多,中國人通常寬容而友好,以禮相待且注重禮尚往來。“如果中國人願意,完全可以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他們隻想要自身的獨立自由,不想獨霸天下。”中國有可能在其他國家的逼迫之下為自由而戰,但是,即便有着幾千年的帝國史,中國人卻并不熱衷帝國霸業。中國曆史上雖然有許多戰亂紛争,但中國人性情溫和,愛好和平,對西方的所謂“進步”這個概念也持懷疑态度。
當然,羅素對中國和中國人也并非隻有贊譽之辭。在羅素即将啟程回國的時候,一位名士(據說是梁啟超本人)問他中國人身上有哪些缺陷,羅素指出了三個:貪财、懦弱、冷漠,《中國問題》一書中對這三個缺陷一一進行了解釋和說明。羅素說讓他深感敬佩的是,那位發問的名士聽了羅素的批評不僅不怒,反而欣然接受,并且還連忙和羅素探讨這些缺陷如何進行補救。“這種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正直正是中國最了不起的品質之一。”羅素感歎。
然而,即便是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誇贊,也并沒有令所有人都為之欣慰。魯迅在1925年寫的《燈下漫筆》一文中就以他一貫犀利的眼光說道,“贊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然後,魯迅說,“至于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贊美中國人,則也許别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一個世紀後的今天,中國人似乎依舊有羅素筆下溫和含笑的一面,而中國早已不是那時的貧弱中國了。
參考文獻
1.附錄,1921,“講學社歡迎羅素志盛”,《羅素月刊》,第一期,pp.1-3.
2.Hayot, Eric. 2006. “Bertrand Russell’s Chinese Eye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18, no.1, pp.120-154.
3.魯迅,2005,“燈下漫筆”(1925),《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pp.222-232.
4.Ogden, P., Suzanne. 1982. “The Sage in the Inkpot: Bertrand Russell and China’s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1920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6, No.4, pp. 529-600.
5.Russell, Bertrand.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6.Russell, Bertrand, and N. Griffin. 2001.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Bertrand Russell: The Public Years, 1914-197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作者簡介

孫賽茵,beat365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在南開大學、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和劍橋大學學習,之後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2010年秋回國任教于beat365至今。研究領域為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文學與思想史。研究興趣包括文學的現代性、後殖民文學理論、文場理論、魯迅及五四文學研究、英語文學中的中國叙述及形象等。代表作為英文專著Beyond the Iron House: Lu Xun and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Field (2017 Routledge;2014 TUP)。